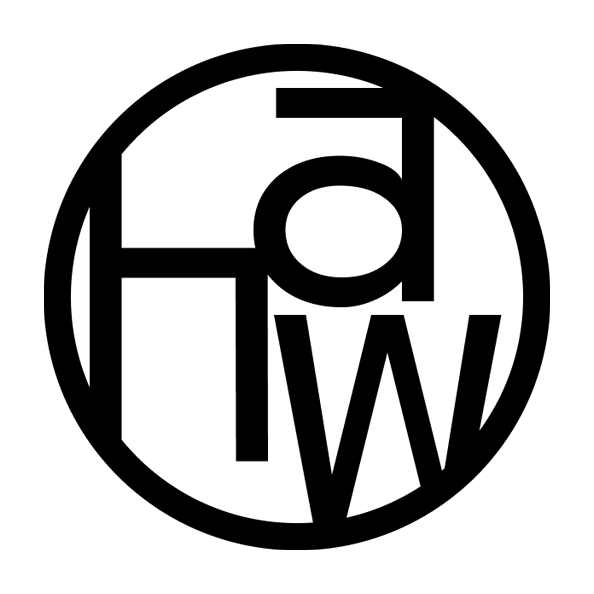Quentin Tarantino 執導的《黑色追緝令》(Pulp Fiction, 1994)不僅是美國獨立製作史上的里程碑,也常被視為重新定義 1990 年代美國電影語彙的轉捩點。影片以片段化、非線性的敘事、類型邊界的拆解,以及高度風格化的暴力影像聞名,在批評界獲得廣泛肯定。
本片通常被視為後現代美學的典型範例。其形式特徵包括敘事的解構、對表面風格與視覺奇觀的強調,以及密集而遊戲性的互文引用,亦即影評中常稱的「塔倫提諾式致敬」(Tarantino-esque homage)。電影一開始便以字典定義與自我指涉的方式,宣示自身是一部關於「通俗小說」(pulp fiction)的拼貼文本。透過拒絕時間順序與線性敘事,影片刻意模糊類型、敘事與「真實」之間的界線,使其與現代主義的敘事規範徹底分道揚鑣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以解構性的敘事與自覺的風格運作,展現後現代文本的典範姿態,也成為研究當代影像文化、互文性與類型再製時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品。
Deleuze 與時間的危機:時間影像與根莖
Gilles Deleuze(1925–1995)在其電影理論中,將影像區分為兩個根本類型:依循感官與運動連結運作的運動影像,與在此連結斷裂後得以直接呈現時間的時間影像。他在《電影 I:運動與影像》(Cinéma 1: L’Image-mouvement, 1983)中指出,經典敘事電影依賴清晰的動作—反應鏈條,透過因果與目的性的連續性維繫敘事邏輯。相對地,《電影 II:時間與影像》(Cinéma 2: L’Image-temps, 1985)則論述現代電影如何在連結破裂之後,使時間本身浮現為影像的直接內容,超越了行動的框架。
大多數犯罪電影皆屬於運動影像的範疇,透過行動序列、調查線索與因果推進來組織情節。然而, Tarantino 的《黑色追緝令》以非線性的結構瓦解了經典敘事對順序與因果的依賴。事件的片段不再按照時間排列,而以跳接、迴返與互文性構築出一個破碎的時間場。觀眾不再追隨行動的指向性,而被迫重新面對時間的斷裂、重組與自我展示。Tarantino 在此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影像邏輯,可被視為「塔倫提諾式時間記號」(Tarantinian chronosign)——時間不只是背景,而成為敘事運作的主體(圖 1)。

Deleuze 所謂的「反常運動」(aberrant movement)在這部電影中獲得具體呈現。影像不再穩定地接續下一個動作,而是透過非預期的切換、自我指涉的段落、暴力的突然爆發或語言的無目的延宕,使觀眾脫離對行動線索的依賴。時間因此不再被行動壓縮,而在影像中以自身的形式展開。觀眾進入一個需要重新組織事件的精神場域,在其中,時間的跳接成為敘事的主要節奏,而非附屬於動作的維度。
在《黑色追緝令》中,時間並不通向某個統一的結局,也不提供倫理或因果的最終整合。它呈現的是 Deleuze 所描述的「時間的晶體」(crystal of time)——現實與虛擬、過去與現在以不穩定的方式互相反射。片段之間的連接並非以單一方向運作,而是形成多重入口與多重出口的場域,使意義在時間的折射中游移。Tarantino 的電影語法由此超越犯罪類型的傳統邏輯,將觀眾置於一個直接面對時間、面對影像生成條件的觀影位置。
不共存性與水晶相
Deleuze 指出,時間影像讓影像充滿時間,使其對自身而言呈現差異。影像不再只是動作的延伸,而是被過去與未來滲透,成為一種「既在又不在」的狀態。Tarantino 在《黑色追緝令》中運用敘事的「不共存性」(incompossibility),將多個彼此排斥的「現在」並置,使事件不再構成單一的編年時序,而構成多個無法化約為統一時間流的異質時間平面。
Vincent Vega(John Travolta 飾)的死亡與後續的再現,是「水晶相」(crystal-image 或 hyalosign)最鮮明的例子。Deleuze 在《電影 II:時間與影像》中將「水晶相」描述為「實際與虛擬的共存」——任何影像都同時包含一個存在於現在的實際層,以及一個在過去與未來振動的虛擬層,兩者互為鏡面。Vincent 的身體正呈現了這種非對稱的鏡像構造。
在 Butch(Bruce Willis 飾)的公寓裡,Vincent 被槍殺,觀眾確認了他的「死亡」;然而在電影後段的餐廳場景,他又再度活著。若以線性時間閱讀,他的存在呈現出三重狀態:已死、活著、並存於時間的裂縫之中。Vincent 的本體論位置不再穩固,而是被分配到多個相互競逐的現在。他的生與死不依賴因果,而由觀眾的觀看位置所決定。對 Deleuze 而言,他成了「總是已經被偽造的角色」(always-already falsified),因為每一次出現都挾帶著對自身的否定。身份無法以固定敘事定義,而是以事件形態存在。
Butch 返回公寓取回父親手錶的段落,提供了另一個水晶相的構造。手錶的擁有、遺失、尋回,都不是線性的連續,而是以「當下的高峰」(peaks of the present)形態發生。這些高峰彼此映照,在敘事的玻璃結構中互相回應,使時間成為回音式的延展。Deleuze 在《電影 I:運動與影像》中稱此為「反常運動」,即影像從時間中出現,而不是從空間中移動而來。Vincent 從浴室踏出面對 Butch 的鏡頭,就是典型的反常運動。他的出現不屬於房間的邏輯,而屬於時間的邏輯。他從「未來」出現,也從「過去」返回,並同時佔據「現在」。觀眾看到的並非人物在空間的位置,而是時間層的交錯。
在 Deleuze 的架構下,Vincent 的生與死不再構成對立。他成為一個在晶體結構內振盪的影像,既是實際的(死於浴室),又是虛擬的(在餐廳中持續活著),並在兩者之間不斷折射。他的身份因此不是心理或敘事的產物,而是時間自身的產物。電影透過拆解因果與時間序列,使時間成為一個塑造角色存在狀態的主體力量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由此展現出 Deleuze 所言的水晶相:一個能使時間的不同面向以鏡像關係互相折返的結構。Tarantino 透過敘事的不連續,揭示事件在時間中的複數棲位,使每一個影像都同時包含自身與其對立面。Vincent Vega 作為時間的碎片化產物,具現了 Deleuze 對影像本體的核心主張——影像不是事物的呈現,而是時間的運動在感知中的形態。
根莖結構與生成
《黑色追緝令》的非線性、片段化敘事以根莖(rhizome)的方式運作。Deleuze 與 Félix Guattari(1930–1992)在《千高原: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》(Mille Plateaux: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, 1980)提出根莖作為與樹狀秩序相對的組織原理,一種以連接、異質性、多重性、非指義性斷裂、製圖與反描摹為基礎的動態網絡。影片的三條故事線透過跳接、交疊與反覆呈現,展現了這種連接邏輯,使敘事不再依賴中心軸線,而以多重入口與出口構成。
觀眾在觀看過程中形成自我導引的地圖式閱讀。事件之間的連結不由時間順序決定,而在於觀眾將哪個片段視為起點、哪個片段視為延伸。故事線的彈性允許觀者自由重組事件,形成具有可塑性的敘事拓撲。觀影因此不再是解讀預先規定的線性意義,而是生成的過程,觀眾的位置與視角在敘事的網狀結構中不斷重新配置。
Deleuze 與 Guattari 在《千高原: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》中將根莖視為開放的材料場域,沒有中心,也沒有明確的起點與終點。《黑色追緝令》在影像結構上顯示了相同的運作方式。Jules(Samuel L. Jackson 飾)、Vincent 和 Butch 的段落不屬於任何形式的敘事階層,彼此在影像中保持等值。沒有角色被授予優先地位,沒有任何情節宣示為「主軸」。觀眾的情感與認知焦點在每一段落被迫重新校正,角色的倫理位置也隨之變動,形成多重的敘事中心。
傳統犯罪電影的線性敘事往往以主角的道德、命運或成長作為引導,但 Tarantino 摒棄這套編排,讓事件之間的連接性取代因果。故事不引導觀眾抵達某個整合性的結局,而是讓影像在根莖式的延展中產生新的意義。觀者不再只是觀者,而是在影像連接的過程中成為生成中的主體,位於作者與作品之間的光滑空間(smooth space)中。
非線性的敘事不僅是風格選擇,更具哲學意義。它拒絕敘事中心主義,拒絕將事件納入單一方向的目的論結構,讓影片成為運動中的系統,沒有統一的敘事權威。每個片段都帶有獨立的強度,沒有任何段落能為其他段落提供終極解釋。觀眾面對的不是一條道路,而是一片地景;不是一條敘事線,而是連接的網路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最終展現出根莖作為電影形式的力量:敘事不以收束為目標,而在連接的持續生成中展開,讓意義在差異與多重性之中流動。
Tarantino 作為 Deleuze 的「偽造者」
「偽造者」(falsifier)的概念在理解 Tarantino 的電影位置時具有關鍵意義。Deleuze 曾以此詞指稱他與 Guattari 的關係,強調「偽造」不是破壞,而是創造性事件,是對既定秩序的偏移與偏軌。偽造者並非摧毀真理,而是揭露真理的可變性,迫使思想面對自身邏輯的限度。
在此語境下,Tarantino 的電影實踐映照了 Deleuze 所定義的偽造者位置。他作為通俗文化與資本主義影像機器的深度參與者,運作方式明顯與 Deleuze 的「殉道者導演」譜系(如 Ozu、Bresson、Tarkovsky)形成對照。這個對照並不構成否定,而是提供檢驗 Deleuze 電影思想的極端條件。流行文化的密集挪用、暴力的形式化、非線性的敘事碎片,都使 Tarantino 的電影成為測試時間影像概念的試金石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的時間結構與敘事節奏展示了 Deleuze 的電影符號學如何跨越藝術電影的疆域,進入商業大片的語法之中。不共存性、反常運動、水晶相等概念並未因影片的通俗性而失效。角色的存在位置持續偏移,事件無法被統一時序收編,觀眾被迫在碎裂的現在中進行組構,這些現象使 Tarantino 的電影獲得了意料之外的哲學密度。
偽造者的核心角色在於擾動穩固的秩序,讓看似自洽的理論在新的環境中重新獲得生命。Tarantino 正是以此方式重新點亮 Deleuze 的時間理論:他並未延續「影像作為精神運動」的傳統,而是將影像置入流行文化的扭曲鏡面,使理論在與通俗影像的摩擦中獲得新的張力。他所呈現的並非「符合 Deleuze 的電影」,而是在 Deleuze 之外運作的影像機器,證明時間影像的邏輯能延伸至更為雜訊、混合、被市場力量牽引的領域。
Tarantino 作為偽造者,使《黑色追緝令》成為一次對真實、對敘事、對時間的重新試驗。他不再是某套電影理論的例證,而是促使理論轉向的引爆點,使思考不得不面對影像在文化機器中產生的新能量。Deleuze 的時間哲學在此不再固定,而進入流變狀態,顯示偽造行為本身就是理論的再生。
Derrida 與在場的缺席:解構與文本的延異
Jacques Derrida(1930–2004)的批判方向始終集中於拆解「標誌中心主義」(logocentrism)與「在場形而上學」(metaphysics of presence)。他指出,西方思想慣常假定語言背後存在一個不延宕、不受媒介干擾的真理核心──一個「起源」或「中心」──所有意義都被視為從那個源頭延伸出來。Derrida 的解構企圖瓦解這種幻象,揭示所有意義都依賴延異(différance)、依賴無限可替換的符號鏈條,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動的本質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以極具策略性的方式推動這種解構思考。影片充滿大量未加解釋的細節、突然出現的象徵、荒誕的旁枝敘述,讓尋求中心意義的觀眾落空。最鮮明的例子是那只散發金色光芒的手提箱。它被設定為敘事的焦點,却永遠不展示其本體。手提箱的光芒吸引所有人物,也吸引觀眾,具備強烈的「意義核心」效果,但它的內部始終被隱蔽。Tarantino 藉此製造了一個近乎純粹的「空白中心」。
Derrida 在評論傳統語言哲學時提出「超越性所指」(transcendental signified)的概念,用以描述被視為語言之源的絕對意義。《黑色追緝令》的手提箱將此結構徹底抽掉。它拒絕賦予任何特定答案,使得追尋真相的衝動不斷延後,形成延異機制。觀眾越期待「答案」,空缺越強化其存在。意義因此不在事物本身,而在符號與符號之間的滑移。
Tarantino 的敘事策略使手提箱成為一個典型的虛位符號(floating signifier)。它不是被設計為解謎的物件,而是作為意義游移的發動點。每一個角色看待手提箱的方式都不同,而這些差異構成影片意義生產的真正場域。手提箱的「缺席」反而成為影像結構的中心。Derrida 在《書寫與差異》(L’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, 1967)指出,文本不依賴起源,而在引用、轉化與差異化中運作。《黑色追緝令》正以影像的方式執行這一論點。
手提箱沒有答案,因為答案從未重要。重要的是觀眾在追尋答案的過程中如何被迫意識到中心的撤退、起源的崩解以及意義的漂浮。電影透過這個策略,使觀眾與 Derrida 的哲學站在同一條思辨線上:意義無法被鎖定,所有中心都是代用品,所有文本都指向另一個文本,而從不指向最後的真理。
延異與銘痕在通俗對話中的體現
延異(différance)指涉意義生成時的雙重運動:意義在符號鏈中被不斷推遲,同時又因差異而得以形成。意義無法在瞬間呈現,而必須在差異化過程中湧現;它從不在場,而是依賴符號間的距離。銘痕(trace)則指向被排除的在場之影,是被語言隱蔽卻持續作用的殘留。Deleuze 的時間影像關注影像內部的虛實折射,而 Derrida 的銘痕揭示語言內部永遠存在的「他者聲音」。兩者皆指向意義無法抵達純粹本質的結構。
Tarantino 的電影語言將延異的運作顯現為可感知的影像事件。對白中的閒聊、流行文化引用、暴力前的停頓、語意在談笑間滑移——這些語言片段形成頻繁閃爍的能指運動,使意義不會在任何單一對話中被固定。人物的言語不意圖通往深度,而是作為語言差異的場域,在滑動與延後中產生強度。意義不落地,而在語言的空氣中振動。
Jules 背誦《以西結書》25:17 的段落,是銘痕運作最具代表性的片刻。引文內容大多出自 Tarantino 的編造,僅借用了聖經語氣。然而觀眾與角色依然感受到來自聖典的重量,並非因為引文本身,而是因為語言中殘留的權威銘痕。它看似神聖,但其「神聖性」只在語言的後設外觀上存活。Jules 的表演將這段文本拉離其所宣稱的來源,語言的力量來自缺席的起源,而非文本原貌。解構(Deconstruction)在此顯露:權威不植根於起源,而是一系列銘痕在語境中重新被組裝。
引文不提供安定的意義。Jules 先以此段落作為暴力儀式的開端,後來又在餐廳場景中賦予它全然不同的倫理轉向。其語意隨語境流動,顯示出符號的不可自足性。每次背誦都帶著前一次的影子,但沒有任何一次能宣稱掌握了決定性的「真理」。聖典的銘痕與世俗語境的雜訊混合,使這段話成為延異的現場。
影片的非時間順序設計延伸了這種延異結構。觀眾無法在單一時間軸上安置 Vincent 的倫理狀態或角色意義。因死亡場景與餐廳場景的距離被摺疊,觀眾的理解隨觀看順序而改變。每次 Vincent 的再現都削弱前一次的確定性,形成意義的連續偏移。角色不再擁有固態的心理與道德位置,而在時間的斷裂中不停被重新書寫。
敘事的跳接構成延異的時間拓撲:意義總是延後抵達,從未在場。沒有任何一個段落能宣布故事的中心,也沒有任何場景能成為解釋其他片段的基礎。Tarantino 透過剪輯與結構的偏移,使觀眾在意義的滑動中被迫放棄尋找單一解答。電影轉化為語言哲學的實驗場所,讓延異的運動不再僅是語言的內在邏輯,而成為影像敘事的可視化狀態。
意義在片段的連接間自行生成,不靠起源,而靠差異;不靠本質,而靠銘痕。解構在《黑色追緝令》中不僅是理論,而是以敘事、角色意識、語言碎屑、影像節奏組構的運動。影片因此呈現了 Derrida 所言:「沒有在場的起源;只有銘痕之間的互相指涉」。
延異與非線性敘事的關係
解構指出,意義無法在單一時刻被確定,必須在差異與延遲中展開;延異(différance)因此同時關涉語義的位移與時間的推遲。非線性敘事使延異從語言層面擴張至影像結構,使敘事本身成為延異的動力場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的時間架構不提供一條穩固的編年軸,觀眾接收到的事件總是被重新排序。Vincent 的生死位置依觀影順序而改變,角色的倫理狀態被迫在時間裂縫中流動。場景不再是單向推進,而是在不同的時間平面間折返,使意義依賴事件之間的差距,而非事件本身。Derrida 指出,符號從不自足,它們在彼此的差異中取得位置;在非線性敘事中,影像段落也呈現同樣的邏輯,意義生成仰賴片段之間的距離與回聲。
跳接與時間折疊使觀眾無法獲得「完整的當下」。每個段落都攜帶前段與後段的影響,角色的言語與行動因順序的改變而產生不同的解讀。場景之間的縫隙因延遲而充滿語義張力,在等待下一個片段填補的過程中產生新的理解可能。敘事時間被拆散為多個未被完成的現在,使意義在反覆的延後中推進。
非線性結構讓影片成為延異的視覺化形式。意義不在特定片段內部,而在片段之間的空隙;不在單一敘事線中,而在多條線的交織中;不在因果關係內,而在因果的崩解與重新排列後的縫隙中。Derrida 的語言哲學在此轉化為影像哲學:意義不斷被遞延,不斷偏移,不斷在不同的時間位置上出現,卻無法被固定。
觀者不再面對一條可遵循的時間線,而是置身於差異化的時間場域。意義生成不再依賴起源,而依賴觀看的位置。觀眾每一次重新編排敘事,都使意義產生轉向。非線性敘事因此成為延異的電影機制,使時間本身成為意義生產的核心。
影片的時間邏輯證明,意義從未在場,而是在延遲與差異中展開;非線性敘事讓延異的運作可被直接觀看,將語言哲學轉化為時閾的經驗。
道德與正義的解構
Derrida 在談論解構與倫理時,總是提出一個關鍵悖論:正義(justice)必須被無限追求,卻永遠無法完全抵達。他將正義視為「不可計算的要求」(the incalculable demand),而非可被制度化的法律。真正的正義始終在未來,始終在延遲之中。倫理行動的價值不在於完成,而在於面向無法被封閉的責任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呈現了一個沒有穩固道德軸線的世界。人物的行動既無法完全歸類於「善」,也無法被視為單純的「惡」;敘事本身打碎了對救贖的即時承諾。黑幫人物所奉行的「專業倫理」(professionalism)、忠誠與尊重,乍看是一套自足的道德規範,卻不斷在細節中自行瓦解。Vincent 自以為保持冷靜與專注,卻因輕率的判斷導致無法逆轉的後果。他所相信的「原則」並未保證更好的行動,而只是暴露了行為者對自身規範的脆弱掌握。
道德秩序在此呈現出解構的運作邏輯。Derrida 指出,等級制的道德分類依賴中心與反中心、起源與派生的結構。《黑色追緝令》透過高度互文化的暴力與偶發性事件,使任何道德定位都無法安定下來。角色的倫理位置在瞬間轉移,沒有誰能占據決定性的高度。善惡並非二元,而是影像中的漂浮記號。
Jules 在餐廳場景作出的行動常被視為影片的倫理焦點。他決定終止暴力生涯,宣布開始「行走於地上的義人之路」。然而,由於敘事的非線性編排,這個轉折不再屬於某種因果序列,而是被獨立地安置在敘事的斷裂區中。觀眾無法追蹤其後果,也無法借助「回溯—結果」的傳統型敘事來理解其意義。選擇只在語言與影像的當下運動中顯現。
Derrida 的倫理觀強調,任何看似穩固的倫理行動都帶有偶然性,它是在語境、銘痕、記號與未被決定的因素交織中形成的「拼裝」(bricolage)。Jules 的轉向正符合這種倫理觀。他的言語吸收了《以西結書》的殘留銘痕,又借由個人恐懼、表演強度與暴力的即時情境被重新定義。決定不是來自一個中心,而來自符號在語境間的流動。
Jules 的道德自我並未獲得圓滿完成,它只呈現為能指的運作。他的倫理位置處於未完成狀態,一如 Derrida 所說,正義只能在不斷推遲之中保持其要求。Tarantino 以敘事的崩解展示倫理的非封閉性,使「選擇」成為一次事件,而不是固定結局的產物。角色與觀眾都停留在延異的張力中,在斷裂的時間裡探尋倫理的可能性。
非線性敘事中的倫理時態分析
倫理判斷通常依賴線性的時間結構:行動先於結果,責任透過因果鏈條被確認。這是法律、神學與道德哲學普遍採用的時態模型。然而,在 Deleuze 與 Derrida 的思想中,時間不再只是背景,而成為倫理事件的組成因素。Deleuze 指出,事件在時間的裂縫中生成,而非在目的論式的連續性中展開;Derrida 認為,責任根源於無法完成、無法計算的未來導向。兩者都使傳統倫理學依賴的連續時間觀失去基礎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以影像呈現倫理時態(Ethical temporality)的解構。非線性敘事令行動與結果脫離可追蹤的順序,角色的倫理位置無法建立在穩固基礎上,因為某些行動未必導向必然後果。Vincent 的死亡並未形成最終結局,反而在後段敘事中被逆向抵銷,使其倫理狀態保持不穩定。死亡發生於前段,但角色在後段仍持續存在於世界中,倫理位置因此停留在未被完成的現在。
在此時態條件下,倫理行動的意義無法以因果鏈條衡量。Butch 的決定、Jules 的轉向、Mia(Uma Thurman 飾)的生死危機,各自被安置於獨立片段,無法透過固定的時序產生連續的倫理軌跡。倫理的意義來自主體在行動當下的語境力量,而非後果。
影片迫使觀眾以不同方式理解倫理。敘事不提供穩定後果,倫理判斷依賴觀看視角,而非故事結尾。Derrida 強調,倫理的核心在於回應不可預期的他者,是面向未來的姿態,而非遵循規則。非線性敘事將此未決性轉化為影像運作,使角色的道德姿態呈現為事件,而非可累積的結果。
Jules 在餐廳的選擇表現出倫理時態的運作。他的決定無法被收斂至任何結局,也無法被後續情節驗證。轉向停留在事件的現在,在語言、情境與身體的邊界形成震盪。倫理價值依附於此刻的事件密度,正義的召喚指向未來,而非敘事中的收束。
非線性敘事揭露倫理的根本運作:倫理不是穩固的定位,而是時間裂隙中的生成。影片讓倫理脫離因果秩序,在破碎的時間場中保持開放。觀眾在觀看人物行動的同時,也看見時間如何形塑倫理的可能性。倫理時態在影像中浮現為可被辨識的結構,使正義的延宕、責任的未決與行動的偶發都成為敘事材料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不僅重新配置敘事時間,也重新配置倫理時間。角色與觀眾都被置於未完成的現在,在延遲與差異的運動中尋找倫理位置。倫理不依賴敘事收束,而依賴時間裂縫;不依賴本質,而依賴事件。非線性結構使倫理時態成為故事核心。
後現代狀況:擬像、拼貼與超價值的批判
《黑色追緝令》運作於 Jean Baudrillard(1929–2007)所描述的「擬像」(simulacrum)領域。在此領域中,現實不再作為原本的世界存在,而是被一組由媒體、影像與文化引用構成的符號矩陣所取代。影片從片名開始就將自身定位為低俗文化的再生產裝置。Pulp 指向廉價紙漿雜誌的視覺與敘事傳統,也顯示它的美學立基於既存符號的再利用與再組裝。敘事並非從生活中提取素材,而是從預先存在的文化檔案中運作。
影像與經驗在電影中透過「無限循環的媒體引用」被重新組織。人物的語言與行動以影視典故為坐標,Mia Wallace(Uma Thurman 飾)背景中的虛構節目《狐狸特攻隊》(Fox Force Five)便是最鮮明的例子。劇中人物的自我理解和互動方式大量依靠對經典電影、電視節目、品牌、流行音樂的引用,使社會互動顯得如同再生產一組永恒存在的符號矩陣。影片透過這些引用展示了對話、風格與情感如何被媒體邏輯所殖民,使真實生活淪為影像的分支。
Tarantino 讓虛構與生活失去疆界。他不將電影呈現為對世界的再現,而呈現為世界本身所運行的模擬結構。在此結構中,暴力行為、生命危機與日常對話以平面化的方式並置。Vincent 和 Jules 在槍擊前討論「法國的四分之一磅起司」,或在處理屍體的過程中爭論禮儀與態度,便呈現了這種符號稀薄化的效果。暴力失去悲劇性,而被吸收進風格化的美學邏輯。戲劇性的情境與無關緊要的日常語彙交疊成為另一種「滑稽病態美學」,象徵意義在模擬時代被過度產生而最終內爆。
Baudrillard 指出,在擬像階段,符號的運作不再指涉真實對象,而是指涉其他符號。Tarantino 的敘事正體現這套邏輯。角色的自我形塑依賴影像文本,決定的倫理重量被風格稀釋,行動的價值由符號魅力取代。影片的世界不是現實的反射,而是通俗文化、影視典故、語言碎片交互堆積的符號生態。現實因此不再是某種可回返的原點,而成為被無限複製與互文化的集合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不僅呈現一部後現代電影,更呈現後現代世界本身的運作方式。人物的行動由影像教導,情感透過流行文化格式化,暴力以美學語彙取代倫理重量。生活以 pulp 的表層邏輯構成——色彩強烈、語言碎裂、引用無盡。Tarantino 不是關心真實如何被再現,而是展示真實已無法與模擬分離。在該片的宇宙中,真實已被影像徹底吞噬;觀眾所見不再是世界,而是世界的符號迴路。
Jameson 與拼貼的邏輯
《黑色追緝令》是 Fredric Jameson(1934–2024)對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實例化。Jameson 將後現代主義視為資本主義晚期的「時期概念」(periodizing concept),其核心美學不在於反叛,而在於文化邏輯的轉換——從現代主義的批判性姿態移向表層化、空洞化、再利用化的文化生產方式。對他而言,後現代的主導形式是「拼貼」(pastiche),一種失去批判性的空白戲仿(blank parody),僅由風格堆疊與表面效果構成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正運作於這種文化邏輯。類型被拆解並在影像中重新排列:黑幫片、瘋狂喜劇、黑色幽默、血腥恐怖、流行文化段子、電視節目語彙,在敘事中彼此並置。Jameson 所理解的拼貼在影片中成為敘事引擎。Tarantino 並非重返某個歷史風格,而是在文化廢墟中收集碎片,使觀眾面對被商品化與媒介化的集體記憶。電影中的每段對話、舞步、槍擊、奇觀,都像是文化檔案的翻頁,使角色的行動帶有轉述風格的銘痕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與 Jameson 的後現代理論形成互相印證的關係。評論者曾指出,Jameson 對後現代文化症候的描述與 Tarantino 的電影世界呈現通向同一結論的平行線,幾乎成為「預言與其實現」。影片以高度自覺的方式進入後現代邏輯:它知道自己由既存影像與語言構成,並以影像再組裝的形式進行創作。塔倫提諾並不隱藏其操作方式,而讓電影本身成為一個後設文本,對自身的人工性保持透明。
電影的「自我製造」(self-production)因此具有結構性意義。敘事的斷裂、時間的重置、角色的再循環,都讓觀眾看到文本如何在文化檔案之上運作。Jameson 提到後現代文化的「深度喪失」與「情感平面化」在影片中獲得視覺化:角色的語言以引用構成、情緒以風格化節奏展現、暴力以視覺趣味包裝,形成去深度化的互文性景觀。Tarantino 的作者地位因此建立在後設書寫的能力上,他的電影不是對世界的表述,而是影像文化的語法示範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最終呈現 Jameson 所言的後現代文化邏輯:歷史被風格取代、批判被引用吸收、意義被敘事碎片化。它並非後現代狀況的附屬物,而是該狀況本身的運作模型,使觀眾身處文化再生產的流動場域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中的懷舊模式、擬像與後現代時間性
《黑色追緝令》在 Jameson 的架構下,呈現出後現代文化的雙層症候:拼貼與懷舊模式(nostalgia mode)(圖 2)。Jameson 所言的懷舊模式並非回憶某段具體歷史,而是「對過去風格的再程式化回收」,是無法通向歷史經驗的表層化回望。它不是對歷史的感傷,而是對影像檔案的調用。

影片的風格操作正是無歷史指涉的懷舊:1950 年代的西岸爵士、黑幫片的義氣語彙、電視節目結構、Drive-in 餐廳美學、70 年代黑色電影的光影,全部被抽離原始脈絡,成為可任意組裝的風格庫存。Tarantino 的角色彼此交談時,引用的是媒體、節目、偶像文化,而非自身的歷史記憶。歷史被風格取代,懷舊不再是對過去的再訪,而是對符號的再利用。Jameson 指出,後現代文化的懷舊不指向歷史,而指向影像;塔倫提諾讓這一理論變成影像敘事的根本邏輯。
時間政治在此佔據核心位置。Tarantino 解構線性時間,以破碎時間結構使懷舊模式脫離因果的敘事邏輯。影片將過去轉化成可供再混編的材料,使歷史不再延續,而被蒸發為一個可被即時調用的影像儲存庫。這使時間不再具備方向性或修辭功能,而成為一種平面化的排列。角色的生命軌跡因此不再依循因果發展,而在多個不連續的片段中重新配置,觀眾必須在這些片段中自行生成時間感。
Jameson 對後現代文化的分析指出時間的瓦解:庸常與奇觀並置、歷史深度被壓扁、記憶轉化為可再現的風格碎片。Tarantino 在敘事中實現了這種時間的扁平化。角色的倫理位置在片段之間被重新定位;生死的順序不構成命運,而成為時間重排後的可視現象。Vincent 的死亡與「後死」再現、Butch 的手錶情節、Jules 在餐廳的啟示時刻,都無法納入單一時間軌跡,而在影像中形成漂浮的時間島。
這種時間的重寫揭示了後現代主體的困境:歷史無法提供穩固的倫理坐標,而被簡化為文化風格的資源池。Tarantino 以非線性敘事使觀眾經驗 Jameson 所指的「時間性破裂」(temporal rupture):事件不再在歷史中延續,而從影像檔案中被隨機抽取。由此,《黑色追緝令》的敘事成為一個後現代時間模型,將懷舊視為文化自我引用的程序,並將時間視為可任意重組的結構。
影片不僅展現 Jameson 理論,更讓其獲得形式上的體現:歷史被影像吸收、敘事被時間壓縮、主體在平面時間中游移。Tarantino 因此不是歷史的敘述者,而是時間政治的操作者,將感知置入沒有深度、沒有源頭、沒有終點的後現代時間場中。
倫理位置、符號邏輯與後現代文化經濟的超價值系統
影片呈現的倫理運作並非虛無主義,而是依循一組凝聚敘事動力的核心「超價值」(hyper-values)。這些價值構成角色行動的深層框架,遠比個人信念或情感更具支配性。三項主導價值構成影片的倫理骨架:黑幫倫理中的專業態度與忠誠、男性對女性的保護責任、以及消費與交換邏輯支配的經濟價值序列。
黑幫倫理將角色置於契約與分工的網絡中。專業精神與忠誠形成行動基準,使角色的自主性被角色義務所稀釋。男性對女性的照護義務在多個段落出現,形成角色動作的道德光暈,卻也製造了更多誤判與危機。超價值的主導位置最明顯地顯現在經濟序列內。角色行動圍繞交易、協商、履約與補償,將倫理判斷轉變為物化計算。公事包、金錶、毒品純度、黑幫名聲皆落入同一價值網絡,使道德位置與「市場節奏」同步。
Baudrillard 的消費符號學深化了超價值的文化層次。晚期資本主義中的物件已不再以使用或交換為核心,而以符號差異為主導。行動因物件的符號力量而發生,倫理位置也因此被符號化物所牽引。發光公事包成為交換、背叛與救贖的支點,並非因內容物,而因其空洞卻強大的符號能量。金錶凝結代際敘事,使布奇的行動不再依附於倫理必然,而依附於物件敘事包覆的符號重量。
Jameson 所提出的後現代「懷舊模式」揭示了另一層超價值結構。Jack Rabbit Slim’s 餐廳的布景化空間中不包含歷史本身,而是對歷史的表演,形成對「過去的意象」的消費。角色在此經驗的不是懷舊,而是風格本身的消費。舞蹈競賽、仿明星服務生、主題化場景,使互動從倫理議題滑向風格遊戲與姿態呈現。價值在此從歷史意義轉向符號強度,使敘事的倫理維度落入景觀化模式。
超價值的運作嵌入敘事的時間邏輯。非線性結構阻斷因果鏈條,使道德行動脫離結果評估。Vincent 的死亡被非線性結構抵銷,其倫理位置流動且不確定。Jules 的道德轉折停留在事件當下,無法被後續場景驗證,使倫理面向呈現為未完成的現在。超價值在此變成倫理行動的真正重力場,角色在價值序列與符號邏輯中移動,而非在道德法則與因果必然中作用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呈現的倫理現象由此浮現:行動被超價值組織,符號物件提供驅力,時間結構使倫理回應保持開放。角色無法透過結局獲得道德定位,因為倫理不再從結果中產生,而是於事件強度與符號交換網絡中形成。《黑色追緝令》透過此結構,使倫理成為後現代文化經濟中的運動,而非義務論或美德論能夠界定的穩定位置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作為後現代時間與意義裂隙的影像實驗
《黑色追緝令》的敘事運作呈現出 Deleuze 與 Derrida 理論在影像層次的交會。Deleuze 所描述的時間影像裂開了行動與結果的對應關係,使現在被分配到多條非連續序列。敘事因此失去編年基礎,事件被推入不共存性的時間空間內,角色的存在狀態在死亡與存活之間反覆被重寫。這個被切割的時間場提供了 Derrida 延異的運動空間。意義無法依附於單一事件,必須透過其他片段的重新排列而流動。銘痕以此形式滲入敘事,使每一次閱讀都停留在「尚未確定」的狀態。
影片的根莖式結構則打破了標誌中心主義的敘事需求。沒有中心事件、沒有核心角色、沒有最終倫理位置。敘事在各種連接之間生成,觀眾的判斷取決於進入影片的節點。這種構造拒絕重新建立單一的道德領域,使所有價值判斷保持未封閉。影像因此不再尋求圓滿結局,而是呈現時間與意義在後現代文化中的漂移狀態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之所以具有長期文化效力,在於它讓後結構主義的概念進入敘事邏輯的核心位置。形式上的碎裂並非修辭,而是反映影像時代的存有條件。Baudrillard 所提出的擬像結構滲透到角色的價值世界,使行動依附於符號而非倫理必然。Jameson 所分析的懷舊模式使歷史感滑向風格化表演,將現代經驗置於景觀的光滑表面。整體社會結構由超價值運作,角色在符號經濟、黑幫倫理與男性照護義務的張力中調整位置,使道德從未獲得穩固的立場。
影片的敘事選擇因此浮現為哲學立場的宣示。非線性影像呈現的不是風格實驗,而是世界觀:時間的裂縫、意義的延遲、倫理的未決、符號的主導。角色在此結構內無法依靠因果關係定位自我,只能在事件的強度中尋找一時的方向。倫理不再是目的論,也不是普遍法則,而是分散於文本連接點之間的片刻姿態。
《黑色追緝令》最終提供的不是關於犯罪的敘事,而是關於存在如何在後現代條件下運作的模型。影像呈現了一個被擬像包圍、被時間分裂、被符號牽引的環境,在其中,選擇不再依附於穩固價值,而在流動的語境內瞬間形成。電影展示了後現代世界的運行公式:意義因延異而形成,主體因時間裂縫而移動,倫理因符號經濟而重組。其形式與內容的結合,使影片成為後結構影像思考的典範。